《堂吉訶德》:它越是令人發(fā)笑,則越使人感到難過
美國當(dāng)代著名文學(xué)理論家、文學(xué)史家哈羅德?布魯姆在《西方正典》中斬釘截鐵地宣告,“在全部西方經(jīng)典中,塞萬提斯的兩位主人公確實是最突出的文學(xué)人物,(頂多)只有莎士比亞的一小批人物堪與他們并列。他們身上綜合了笨拙和智慧,以及無功利性,這也僅有莎士比亞最令人難忘的男女人物可以媲美。”但塞萬提斯生前從未聽到過類似這樣的評價。如同許多偉大的不朽名著一樣,《堂吉訶德》在甫一問世時并沒有得到足夠重視。“所有人看《堂吉訶德》都在笑,同時代的人瞧不起塞萬提斯,說他寫的東西不倫不類,認(rèn)為沒有比《堂吉訶德》更可笑的作品。這對塞萬提斯打擊非常之大”,陳眾議說。
7月27日,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學(xué)部委員、外國文學(xué)研究所所長陳眾議做客首都圖書館,主講“閱讀文學(xué)經(jīng)典(第二季)”第四講——塞萬提斯與《堂吉訶德》。

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學(xué)部委員、外國文學(xué)研究所所長陳眾議(照片由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提供)
開掛一樣的“倒霉一生”
“我總是夜以繼日地勞作,自以為具有詩人的才學(xué),怎奈老天無情毫不理會。”和當(dāng)時所有的文學(xué)青年一樣,塞萬提斯最初傾心的文學(xué)類別是詩歌與戲劇。但青年人往往會錯把熱情當(dāng)做天賦,和絕大多數(shù)的文學(xué)青年一樣,作為“詩人”和“戲劇家”的塞萬提斯籍籍無名。但相比于塞萬提斯一生的失敗而言,文學(xué)創(chuàng)作起步時的失敗簡直不算什么——
塞萬提斯出生在沒落貴族家庭,父親大學(xué)肄業(yè)后做游醫(yī),一生流離失所又窮困潦倒。塞萬提斯生于1570年,自幼夢想成為榮耀的騎士。1570年他如愿從軍,成為一名戰(zhàn)士,次年參加抗擊土耳其的勒班多海戰(zhàn),在沖上敵艦英勇戰(zhàn)斗時身負(fù)重傷,不幸失去左臂。戰(zhàn)后,塞萬提斯攜帶總督和元帥的保薦信回國,途中遭遇土耳其海盜伏擊被俘虜,并賣到阿爾及爾當(dāng)奴隸。他三次謀劃逃跑沒能成功,終于在1580年經(jīng)由一名神父搭救回到西班牙。此時戰(zhàn)爭已經(jīng)結(jié)束許久,曾經(jīng)的榮耀被人們忘卻,塞萬提斯失去了獲得體面工作的機會,只得在無敵艦隊中做些后勤雜務(wù)。隨著無敵艦隊的瓦解,他很快再次失去工作,并被人誣陷入獄。出獄后,塞萬提斯托各種關(guān)系,找了一份辛苦的稅務(wù)官差事做,并被派到最偏遠的山區(qū)。收稅的回憶絕對談不上美好,一方面無人愿意上繳稅金,一方面又天天挨罵。兩年后,由于儲存稅金的私立錢莊倒閉,塞萬提斯再次入獄。之后,他還曾因沒有準(zhǔn)備好私生女的嫁妝被私生女告上法庭,因家門口驚現(xiàn)無人認(rèn)領(lǐng)的死尸而被警察抓包抵罪。類似這樣的無頭官司,塞萬提斯一生經(jīng)歷了不知多少,世態(tài)炎涼給他的內(nèi)心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烙印。

塞萬提斯畫像(圖片來自網(wǎng)絡(luò))
15-16世紀(jì)的西班牙異常強盛,“無敵艦隊”威震天下,在全球擁有大量殖民地,一船船的真金白銀從美洲運回本土,“錢多得就像花不完一樣”。富裕的西班牙人大量購置島嶼、投資商業(yè),但更多的人像塞萬提斯一樣生活在社會底層,窮得叮當(dāng)響。陳眾議認(rèn)為,這種兩極分化的社會環(huán)境,正是塞萬提斯批判精神的由來。
1602年,塞萬提斯開始創(chuàng)作《堂吉訶德》,當(dāng)時他住在劣質(zhì)公寓房,樓下是小酒館,樓上是妓院。三年后《堂吉訶德》第一卷出版,在西班牙引起了山呼海嘯般的轟動效應(yīng),該卷一年之內(nèi)再版六次,從宮廷到市井,所有人的都在談?wù)撎眉X德騎士的故事。由于寫書所得的利潤全部被出版社獲得,直至1616年患病去世,塞萬提斯依然在貧困中掙扎,去世后連墓碑都沒能立。
《堂吉訶德》:生前寂寞身后名
陳眾議認(rèn)為,在分析小說《堂吉訶德》之前,首先應(yīng)該梳理先前的文學(xué)譜系。
在近千年的中世紀(jì)里,西方忘卻了古希臘羅馬時期光輝燦爛的歷史文化,甚至逐漸失去文字,回到了口傳時代。同時,阿拉伯世界在與中國的交流中,將源自中國的造紙術(shù)和印刷術(shù)廣泛傳播,開啟了百年翻譯運動。把東方的經(jīng)典傳到西方的同時,還把被西方忘卻的古希臘羅馬經(jīng)典又重新翻譯印制了出來,為文藝復(fù)興的繁榮埋下了基石。

新版“網(wǎng)格本”《堂吉訶德》
[西班牙]塞萬提斯 著 楊絳 譯 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9年出版
作為“中世紀(jì)的最后一個作家”和“文藝復(fù)興時期的第一個作家”,但丁的《神曲》既是西方基督教傳統(tǒng)的集大成者,又是人文主義道路上的偉大先驅(qū)。但丁在《神曲》開篇中寫道,“在人生的中途,我發(fā)現(xiàn)我已經(jīng)迷失了正路,走進了一座幽暗的森林……我說不清我是怎樣走進這座森林的,因為我在離棄真理之路的時刻,充滿了強烈的睡意。”在進退兩難、荒野難行的森林中,但丁遇到了獅、豹、狼三種寓言野獸,分別對應(yīng)著西方文化中關(guān)于強權(quán)、淫欲與貪婪的隱喻。當(dāng)全能的宗教失去統(tǒng)攝力量,人性自在的善惡就開始恢復(fù)生機。但丁之后,伊塔大司鐸在《真愛之書》中賦予金錢無所不能的強大力量,薄伽丘則用異于常人的機敏創(chuàng)作《十日談》,展現(xiàn)人與欲望之間的復(fù)雜關(guān)系,而拉伯雷將狂歡化的語言充進巨人的皮囊,將教會丑惡與偽善的面紗無情揭下。喜劇通過驚人的狂歡勢能釋放人們的情感,幽默諷刺和玩世不恭的調(diào)笑很快便充斥了15世紀(jì)的歐洲文壇。而資本的興盛必然帶來信仰的淪落,塞萬提斯通過否定之否定的喜劇《堂吉訶德》,展示了騎士精神在一個新時期的全盤潰敗。
《堂吉訶德》在面世時曾被認(rèn)為是一部用小說寫成的喜劇,被當(dāng)做供人消遣的通俗讀物,充當(dāng)茶余飯后的談資,甚至在西班牙曾流行這樣的說法:誰在那邊笑得直不起腰來,誰肯定在看《堂吉訶德》。陳眾議認(rèn)為,在當(dāng)時的歐洲,小說作為一個新興的文學(xué)體裁尚未得到上流社會的認(rèn)可,處在巴洛克鼎盛時期的詩歌界和戲劇界大都視小說為不登大雅之堂的劣等藝術(shù)。當(dāng)時的文壇泰斗洛佩?德?維加就曾鄙夷地說:“沒有比塞萬提斯更糟的詩人,沒有比《堂吉訶德》更傻的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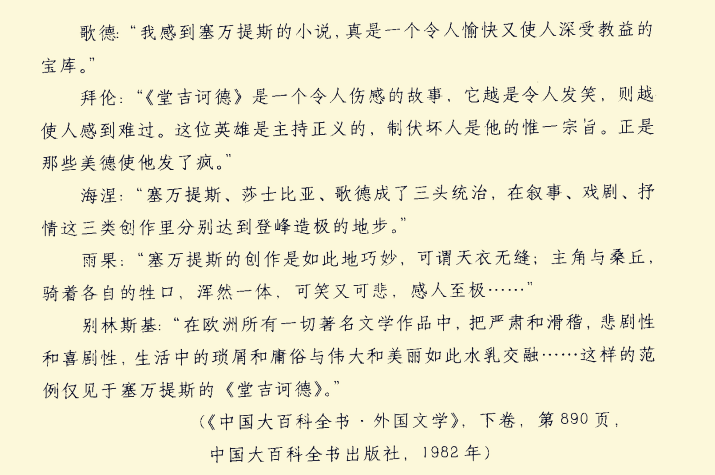
歌德、拜倫、海涅、雨果、別林斯基對《堂吉訶德》的評價,轉(zhuǎn)引自徐葆耕《西方文學(xué)十五講》
但小說本就起自于草莽,市民文化的煙火氣息使小說的世界包羅萬象。盡管在生前被認(rèn)為是不入流的通俗作家,但塞萬提斯身后卻聲名日隆。18世紀(jì),亨利?菲爾丁和薩繆爾?約翰遜認(rèn)為堂吉訶德身上融合了滑稽與崇高這組兩相矛盾的美學(xué)風(fēng)貌。19世紀(jì),詩人拜倫進一步指出“塞萬提斯的偉大就在于他充滿同情地揭示了堂吉訶德的悲劇命運”。
沖啊騎士!和長臂巨人搏斗
《堂吉訶德》是一部文藝復(fù)興時期偉大的人文主義作品,但陳眾議認(rèn)為,這部小說同時也是一部非常懷念中世紀(jì)的、充滿保守傾向的文學(xué)作品。
《堂吉訶德》的保守主要在于他對當(dāng)時的文化采取批判姿態(tài)。塞萬提斯不屑于文藝復(fù)興時期的市民文化,他試圖借助小說人物堂吉訶德去擁抱中世紀(jì)的騎士文化。“中世紀(jì)的標(biāo)志性文化就是騎士文化,所謂的騎士精神,一種是要為自己的王國奉獻一生,要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yè),就像中世紀(jì)的很多傳奇故事;另一種是要維護宗教,譬如《圓桌騎士》,英國傳奇中的梅林術(shù)士,還有像《羅蘭之歌》中的羅蘭。”陳眾議談到,塞萬提斯熱愛騎士文化中的英雄人物,他們忠于上帝和國王,用一生為國家建立不朽功勛。
但在《堂吉訶德》序言中,塞萬提斯卻說騎士小說已經(jīng)過時,要通過《堂吉訶德》把陳舊的一套掃除干凈。陳眾議說,這其實并不矛盾,因為當(dāng)時騎士小說中的騎士往往為了愛情放棄自己的信仰,而塞萬提斯認(rèn)為這種自我拋棄英雄氣概的唯愛情論違背了騎士精神,把騎士文化引向了狹隘與世俗化。

位于西班牙馬德里的堂吉訶德與桑丘塑像(圖片來自網(wǎng)絡(lu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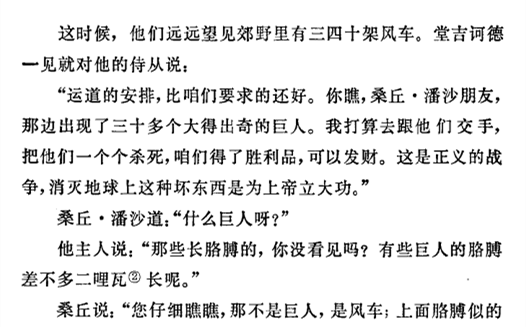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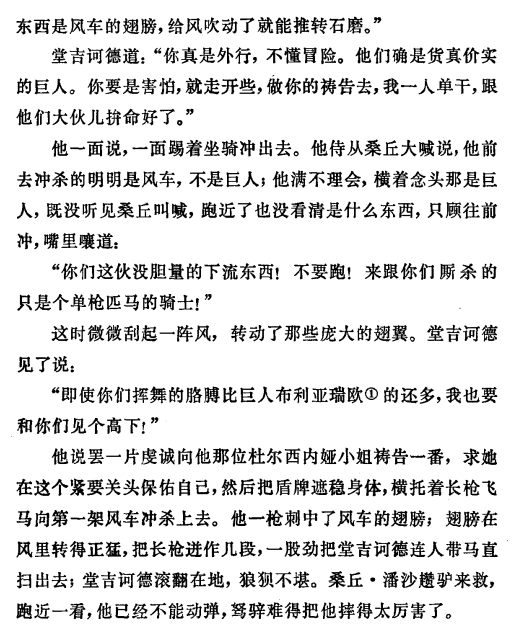
堂吉訶德迎戰(zhàn)風(fēng)車(據(jù)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網(wǎng)格本,1978年版)
小說中堂吉訶德大戰(zhàn)風(fēng)車的片段歷來被人傳頌,成為彰顯主人公性格最鮮明的體現(xiàn)。堂吉訶德和侍從桑丘在一片荒野中看見一排風(fēng)車,堂吉訶德固執(zhí)地認(rèn)為風(fēng)車是一個個胳膊長長的巨人,不聽桑丘的勸告,橫槍飛馬沖殺上去,結(jié)果被風(fēng)車所傷翻滾在地、動彈不得。堂吉訶德性格上的高度分裂由此可見一斑:一方面癲狂可笑,另一方面又有著無畏的英雄主義情懷。而在陳眾議看來,從藝術(shù)描寫的角度讀《堂吉訶德》,小說最大的特點就是用喜劇的方式體現(xiàn)悲劇精神。用一主一仆并行的方式對照建構(gòu)主人公,形成堂吉訶德與桑丘兩個人物形象,開創(chuàng)了人類文學(xué)史上人物形象塑造的先河。“這特別像我們的小品或者相聲,一個捧,一個逗,這兩個配合得天衣無縫。” 桑丘作為反襯堂吉訶德的形象被創(chuàng)造出來,和堂吉訶德形成對比,從側(cè)面再次突出了騎士精神的信仰衰落。堂吉訶德充滿幻想,桑丘處處實際;堂吉訶德學(xué)識豐富,桑丘大字不識;堂吉訶德禁欲苦行,桑丘則是一個享樂主義者。正如朱光潛先生的評價:“他們一個是可笑的理想主義者,一個是可笑的實用主義者。但堂吉訶德屬于過去,桑丘?潘沙卻屬于未來。”

《阿Q正傳》(左)與《豐富的痛苦》(右)
這種對比式的分析,在中國則發(fā)生了另外一重變異。《堂吉訶德》在上世紀(jì)20年代譯入中國,同時有論者也將俄國文學(xué)家屠格涅夫的觀點引入,屠格涅夫?qū)ⅰ短眉X德》和《哈姆雷特》進行對照,認(rèn)為“這兩大名著的人物實足以包舉永久的二元的人間性,為一切文化思想的本源;堂吉訶德代表信仰與理想,漢列忒(哈姆雷特)代表懷疑與分析”。應(yīng)該像哈姆雷特一樣踟躕猶豫、審慎選擇,還是應(yīng)該學(xué)習(xí)堂吉訶德的奮不顧身、沖向“風(fēng)車”,一度成為當(dāng)時思想界的討論的熱門話題。陳眾議說,魯迅的阿Q頗有堂吉訶德的影子,或謂一個毫無理想主義色彩的反堂吉訶德,且阿Q的“Q”恰好是吉訶德的第一個字母。魯迅的確對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有所關(guān)注,他曾說堂吉訶德是“專憑理想勇往直前去做事”,而哈姆雷特“一生冥想,懷疑,以致什么事也不能做”,并曾與瞿秋白共同翻譯盧那察爾斯基的《解放了的堂吉訶德》,一同撰文《真假堂吉訶德》等。除魯迅外,堂吉訶德還走進了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許多作家的筆下,陳眾議認(rèn)為廢名的小說《莫須有先生》受到《堂吉訶德》影響很大,當(dāng)代學(xué)者錢理群更著有《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分析兩個經(jīng)典人物形象的內(nèi)在魅力及對中國現(xiàn)代社會的影響。陳眾議說,當(dāng)下我們既不能過于沖動,又不能優(yōu)柔寡斷,“堂吉訶德的冒險精神很容易導(dǎo)致盲目,哈姆雷特的延宕又很容易讓人一輩子碌碌無為,甚至陷入虛無主義,兩個極端都不適合我們這個時代,而是需要從中找到一個平衡點。”(陳澤宇)
參考文獻:
《西方文學(xué)十五講》,徐葆耕著,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出版。
《經(jīng)典的困頓和蘇醒》,陳眾議,《文藝報》2016年5月11日。
《<堂吉訶德>,一個時代的“精神畫餅”》,陳眾議,《解放日報》2016年4月16日。
《永遠的騎士》,陳眾議,《光明日報》2016年8月5日。
相關(guān)鏈接:
“閱讀文學(xué)經(jīng)典”第二季第一講:巴黎圣母院與《巴黎圣母院》的相互造就
“閱讀文學(xué)經(jīng)典”第二季第二講:人生苦短,先讀莎士比亞
“閱讀文學(xué)經(jīng)典”第二季第三講:曹立波談“紅樓”:林妹妹到底幾歲進賈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