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如風有信 | 巴西當代詩歌:掛在繩上,傳唱在街頭擂臺
“青春詩會”是中國詩歌界最具影響力的品牌活動,是青年詩人亮相的舞臺與成長的搖籃。《詩刊》社從1980年起,已成功舉辦了39屆“青春詩會”,吸納了570多位優秀青年詩人參加,每屆詩會推出的詩人和詩歌,都引起文壇廣泛的關注。
以文化人,更能凝結心靈;以藝通心,更易溝通世界。為以詩歌為媒介傳遞青春的詩意,增進文明交流互鑒,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作家協會將于7月18日至24日在杭州和北京兩地舉辦“首屆國際青春詩會——金磚國家專場”,來自金磚成員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聯酋、伊朗、埃塞俄比亞等國的詩人們,將與中國詩人一道,青春同行,歌詠言志。
開幕式上,將以詩歌朗誦、情境表演、聲樂、舞蹈、戲曲等多種藝術形式,展現金磚成員國的歷史文化和詩意之美。十國詩人將圍繞詩歌創作等相關話題,展開“青春詩會”學術對話。活動期間,各國詩人將領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感受生動立體的中國形象,還將舉行金磚國家青春詩人手稿捐贈儀式,讓詩歌見證不同國家、民族、文化和詩人間的情誼!
“愿如風有信”,“詩人興會更無前”,我們期盼“以詩之名”的“國際青春詩會”,必將是一場如約而至的青春盛會。從即日起,中國作家網將陸續推出介紹參會各國文學和詩歌創作情況的文章,邀請您一起,在各國文學之林來一次青春漫游。
巴西參會詩人簡介

西達·佩德羅薩
Cida Pedrosa
女,巴西共產黨黨員,詩人、小說家、伯南布哥州累西腓市議員。代表作:《紅金剛鸚鵡》、《莉莉絲的女兒們》。曾獲圣保羅藝術評論家協會2022年最佳詩集獎、2020年雅布提年度圖書獎和詩歌獎。

安娜·魯什
Ana Rüsche
女,詩人、小說家、學者、英語文學博士,圣保羅大學文學與氣候危機專業博士后。已出版5部詩集、3部小說。代表作有處女作詩集《撕裂》以及《喜歡紀錄片的我們》《狂怒》,科幻小說《他人即通靈》等。曾獲奧德賽奇幻文學獎、圣保羅文化廳ProAC獎,有作品入圍雅布提獎決選名單。部分作品被譯為西班牙語、意大利語和英語出版。多次參加國內國際文學活動,如紐約美洲詩歌節等。

羅德里戈·維安納
Rodrigo Luiz Pakulski Vianna
詩人、記者、教師。代表作有詩集《讓你記得去海灘的文字》《維阿那》《那不是一座城市》。曾獲2019年馬拉阿獎、2021年巴西國家圖書館文學獎。

朱莉婭·漢森
Júlia de Carvalho Hansen
女,詩人。圣保羅大學文學學士,里斯本新大學葡萄牙語碩士。著有5部作品,代表作有愛情詩集《石榴》、植物詩集《毒樹液或果實》。曾擔任2019年、2022年、2023年巴西海洋文學獎評委,兩次參加巴西帕拉蒂文學節。

蒂亞戈·莫賴斯
Thiago Ponce de Moraes
詩人、翻譯家,里約熱內盧聯邦學院教授。已出版5部詩集和1部散文集,詩集曾入圍2016年雅布提獎短名單。翻譯過現當代歐洲、拉美和阿拉伯詩人的作品。多次參加國內國際文學活動。

盧比·普拉特斯
Lubi Prates
女,詩人、譯者、編輯,圣保羅大學人類發展心理學博士。已出版4部作品,代表作有詩集《黑色的身體》《至今》。《黑色的身體》曾獲巴西ProAC獎及詩歌創作發表扶持基金,入圍第4屆里約文學獎和第61屆雅布提獎。翻譯過美國女詩人瑪雅·安吉羅、瓊·喬丹等人的作品。曾參與組織巴西“我是詩人”女性文學節等活動,擔任巴西海洋文學獎、雅布提文學獎等評委。有作品在阿根廷、哥倫比亞、克羅地亞、美國、法國、瑞士翻譯出版。多次參加國內國際文學活動。

路易莎·羅芒
Luiza Rom?o
女,詩人、演員、學者,圣保羅大學文學理論與比較文學在讀博士。代表作有詩集《莫托洛夫的雞尾酒》《血流成河》《我們這里也保存石頭》。作品入選《當代29位詩人》等多部詩歌合輯。曾獲2022年雅布提獎最佳詩歌獎、最佳作品獎等。多次參加歐洲和拉美詩歌節活動。
在“下沉”中上升:巴西當代詩歌創作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 長聘副教授
樊星
自1922年巴西現代主義運動以來,巴西的詩歌創作總體走上了追求自由表達、擁抱大眾民俗的道路。盡管在20世紀中葉曾短暫掀起形式格律方面的復古風潮,但隨著1964年軍政府上臺,這種風潮也迅速消弭,取而代之的是“邊緣詩歌”(Poesia Marginal)等反抗形式。自此之后,無論是對軍事獨裁的直接對抗與事后反思,還是對再民主化進程后現實困境與社會問題的捕捉與反諷,巴西詩歌創作都具有較為鮮明的通俗化、日常化與口頭化特征,尤其重視對于詩歌音樂性的展示。在互聯網等多媒體平臺的幫助下,通過將書寫的詩轉化為吟誦的詩,巴西詩歌的豐富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得到了更充分的呈現。隨著詩歌創作從精英階層的特權逐漸轉向大眾自我表達的需要,曾經因為種種原因難以獲得出版機會的詩人團體與詩歌類型正成為創作與分享的主力,原先被壓抑的聲音得到釋放,并在更高的舞臺上回響。
掛繩詩:民間詩歌的復興
掛繩詩(Poesia de Cordel)起源于文藝復興時期的伊比利亞半島,當時人們將中世紀游吟詩人的口頭創作印刷后掛在繩上販賣,這種語言淺白、講求押韻的俚俗詩體即得名為掛繩詩。十六世紀葡萄牙開啟對巴西的殖民之后,掛繩詩以口頭形式在新大陸廣泛傳播,并在彼時人口最為集中的東北部地區扎根,成為具有巴西本土特色的藝術樣式。在一個絕大多數人尚不識字的時代,民間詩人的聲音經過口耳相傳不斷擴大,乃至代替成文歷史,成為塑造當地人集體意識的重要媒介,掛繩詩也成為巴西最重要的民間詩歌形式之一。十九世紀末,巴西掛繩詩從口頭創作進入印刷領域,這股熱潮在二十世紀中葉達到頂峰。然而,隨著軍政府上臺以及一批掛繩詩巨匠的陸續離世,這一詩歌形式也逐漸歸于沉寂,以至80年代許多學者宣告“掛繩詩已死”。

掛繩詩
然而,掛繩詩卻在二十一世紀迎來復興。出生于巴西東北部塞阿拉州腹地的維亞納兄弟是這場復興運動的主要推手,兩人既擅長撰寫掛繩詩,也善于為其配圖,出版的作品深受公眾歡迎。1998年,弟弟克萊維森(Klévisson Viana)創辦了以巴西原住民族群命名的圖皮寧金(Tupininquim)出版社,從出版兄弟倆的作品開始,很快成為東北部最重要的掛繩詩出版商,而哥哥阿里耶瓦爾多(Arievaldo Viana)則從2000年起提出讓掛繩詩進入課堂的動議,并收到良好的效果。除此之外,兩兄弟也積極尋求外部合作,通過舉辦掛繩詩比賽、將掛繩詩作改編為電視節目等方式,進一步提升掛繩詩在公眾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與可見度。
作為民間藝術的經典形式,當代掛繩詩的主題幾乎無所不包,既有對巴西東北部習俗傳說的描繪,也有對世界各地故事的挪用。關于這一點,可以在克萊維森的詩作《掛繩詩人的箱子》中窺見一斑:
掛繩詩人的箱子里
有勇敢的故事
無懼無畏的牧民
穩穩坐上馬鞍
偷走主人的女兒
不怕槍手阻攔
選擇為愛而戰
他押韻的冒險
在掛繩詩人的箱子
掛繩詩人的箱子里
有孔雀的故事
傳福音的土耳其人
從兄弟手上
獲得女神的畫像
美麗的克瑞烏薩
被從國外帶來
可憐的青年
看到她便平靜不在
在掛繩詩人的箱子
在節選的兩個詩節中,能夠明顯看到“牧民”“馬鞍”“槍械”等巴西腹地想象中的傳統意象與“土耳其人”“克瑞烏薩”等外來象征之間的對比,而詩人在最后表示箱子里有“適于任何品位的詩行,風格任君挑選”,更明確了巴西當代掛繩詩自由包容的特質。除了簡明的語言表達、順暢的韻律節奏以及對現實話題的關注之外,新時代掛繩詩人的詩作極為豐富多元,其中布勞利奧·貝薩(Bráulio Bessa)與雅里德·阿萊斯(Jarid Arraes)是兩個頗具代表性的人物。

布勞利奧·貝薩
布勞利奧·貝薩于1985年出生于塞阿拉州小城阿爾托桑托市,是巴西東北部文化的積極捍衛者。與大多數詩人不同,貝薩并非以“寫作”聞名于世,而是因“朗誦”而為大眾熟知。2014年,為了回應部分人對于東北部群體的偏見與歧視,貝薩發布視頻,演繹前輩掛繩詩人布勞利奧·塔瓦雷斯(Bráulio Tavares)與伊萬尼爾多·維拉諾瓦(Ivanildo Vilanova)的作品《獨立東北》(Nordeste Independente),短時間內即收獲了50萬次播放。在此之后,貝薩又成為電視節目“沾糖詩歌”(Poesia com Rapadura)的常駐嘉賓,在節目上朗誦的原創詩歌隨后結集成他出版的第一部詩集,他本人也一直保持較高的網絡曝光度。
貝薩的成名之路無疑反映出網絡及視頻時代的流量邏輯,但同時也印證著掛繩文學傳統的口頭與集體特征。一方面,大多數人都是通過聆聽而非閱讀接觸貝薩的作品,這也在無形中擴大了其作品的受眾范圍,尤其是那些并未接受太多教育的群體;另一方面,貝薩的成名之作都有著普遍性的主題,能夠引發幾乎所有人的共鳴。他最受歡迎的詩作《重新開始》(Recomece)的開頭如下:
當遭遇生活的重擊
靈魂血流不已
當這個沉重的世界
傷害并碾壓著你……
是時候重新開始
重新開始戰斗。
當四周陰暗不清
沒有一絲光明
當你只有懷疑
一切都無法確定……
是時候重新開始
重新開始相信。
盡管僅節選了兩個詩節,但可以明顯看出《重新開始》是對面對困境之人的安慰,詩人本人也聲明他愿將詩歌比作擁抱,能夠在不知傷痛何在的情況下撫慰靈魂。如果說貝薩的詩歌注重給予所有困境之中的人以溫情與希望,90后女作家阿萊斯的作品則始終關注女性尤其是黑人女性群體的真實命運。在代表作《十五首掛繩詩講述巴西黑人女英雄》(Heroínas Negras Brasileira em 15 Cordéis,2017)中,阿萊斯用史詩般的筆調講述了巴西黑人女性代表所遭遇的實際困難,從反抗奴役的非洲公主到居住在貧民窟的黑人女作家,大部分人始終遭受忽視與遺忘,阿萊斯則用詩將她們帶到臺前。

《十五首掛繩詩講述巴西黑人女英雄》書影
值得說明的是,盡管阿萊斯的祖父與父親均為掛繩詩人與木刻畫師,受家庭影響,她從小便浸潤于民間藝術之中,但她同時也很早便接觸到卡洛斯·德魯蒙德·德·安德拉德、曼努埃爾·班德拉、費雷拉·古拉爾等二十世紀巴西經典詩人的著作,這使她的創作不僅局限于掛繩詩,也包括其他類型的詩歌與長短篇小說等體裁,均取得了市場與學界的肯定。考慮到阿萊斯的創作始終圍繞著黑人女性展開,可以說她的成功不僅佐證了掛繩詩的復興,也是女性文學發展的有力注腳。
女性詩:群體意識的形成
2021年,巴西著名作家、文學批評家埃洛伊薩·布阿爾克·德·奧蘭達(Heloísa Buarque de Hollanda)主編的詩集《當今29位女詩人》(As 29 Poetas Hoje)問世,收錄了包括雅里德·阿萊斯在內29位女性詩人的作品,其中最年長的迪妮婭(Dinha)出生于1978年,最年輕的雷吉納·阿澤維多(Regina Azevedo)出生于2000年。在奧蘭達為詩集撰寫的前言中,除展現當前巴西青年女性詩人創作的全景之外,更回望了上世紀70年代至今巴西女性詩歌的創作歷程,清晰勾勒出代際間的傳承與同輩間的共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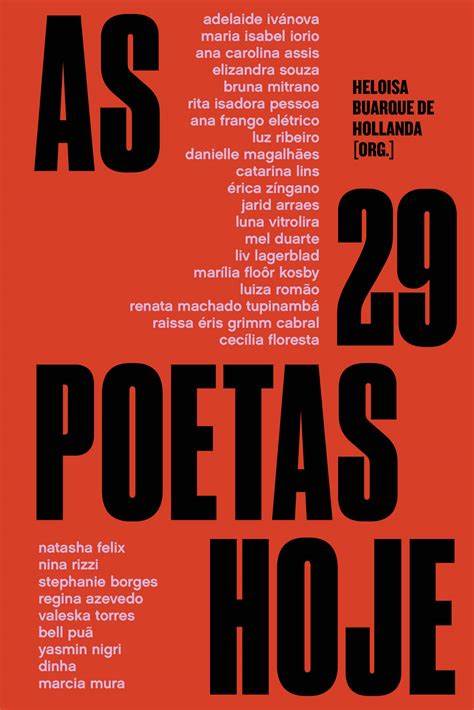
《當今29位女詩人》書影
傳承的源頭可以追溯到1976年。當時巴西文壇正處于軍政府文藝審查制度的高壓之下,奧蘭達編纂了現已成為經典的詩集《當今26位詩人》(26 Poetas Hoje),收錄了撰寫反抗詩篇卻缺少公開出版機會的“邊緣詩歌”創作者,其中包括當時年僅24歲的女詩人安娜·克里斯蒂娜·塞薩爾(Ana Cristina César)。塞薩爾的出現對于巴西的女性詩歌創作極為重要,她反對男性批評者對于女性詩歌所謂“朦朧”“細膩”“敏感”的定義,提倡打破沉默,言說真正的女性問題,并不避諱對于身體、私密的直白描寫,正如她在一則書評中所說:“那些寫作花朵、月光、溫柔、流暢的地方,理應讀作干燥、粗糲、直白的暴力。”

安杰麗卡·弗雷塔斯
塞薩爾31歲時自殺身亡,詩集《在你腳下》(A Teus Pés, 1982)作為其生前唯一正式出版的著作,因詩歌與散文形式的結合、碎片化的表達以及私密性的自白,對巴西年輕一代女性詩人產生了強烈的沖擊與巨大的影響,如在當今巴西文壇負有盛名的安杰麗卡·弗雷塔斯(Angélica Freitas)。在弗雷塔斯的經典詩集《子宮如同拳頭一般大小》(Um útero é do tamanho de um punho, 2012)中,能夠清楚看到對女性境遇的深刻體察,借由各種出其不意的意象組合,揭示女性千百年來被馴化、被評判、被剝削的命運。以詩集第一部分“一個干凈的女人”(Uma Mulher Limpa)為例:
因為一個好女人
是一個干凈的女人
如果她是個干凈的女人
就是個好女人
千百萬年前
女人雙腳站立
那時的她兇猛骯臟
兇猛骯臟并且吠叫
因為一個兇猛的女人
不是一個好女人
而一個好女人
是一個干凈的女人
千百萬年前
女人雙腳站立
她溫順,不再吠叫,
她又溫順又好又干凈
此處的“干凈”顯然指向對于女性身體的規訓,同時“清潔”的要求又關乎道德,從而形成對于女性多個層面的禁錮,這正是作者本人面對的真實困境。在談及這部詩集的創作時,弗雷塔斯曾提到,作為一名詩歌讀者,她意識到巴西缺少關涉女性議題的詩作,而為了精確呈現女性自我,需要重新創設語言,打破傳統的詩歌規范。
作為女性主義詩歌的破冰者,塞薩爾、弗雷塔斯為新一代女性詩人展示出書寫自身的可能,讓后者更具勇氣與意識,尋找并發出女性的聲音。有了前輩榜樣的引領,加之近十年來女性運動在巴西的不斷涌現,尤其是互聯網平臺上的熱門話題與活動宣傳,在巴西當代的青年女性詩作中,自身性別的主體性視角已得到充分展現,風格類型極為多樣。僅以《當今29位女詩人》收錄的詩作為例,對于上文已經提到的阿萊斯來說,自我表達可以是一首掛繩詩,其中雖反復強調“我并非出自這首掛繩詩,不出自我寫下的詞匯,或可能提出的格律,我是一個受限的動物”,但卻以“意義已經腐敗,而我意圖抗爭”開頭,以“然而我的意義,我打算親自構建”結尾;而在印第安詩人雷娜塔·馬查多·圖皮南巴(Renata Machado Tupinambá,1989)看來,自我則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風格,如她在《母系少女》(Matriarcal Cunh?)一詩中所寫的那樣:
你們以為看得見我?
你們以為看得見我?
我是微光
明亮
是人民的歌謠與自由
我手中握有情誼
我是街頭、農場與社區
流淌的血液
你的心因謊言鮮血淋漓
我的心每天死去,又重生
我不是波提拉族印第安人
我是阿拉提吉拉族
所以你可以將武器
扔向我的頭顱
你殺不死我
我說扔啊快扔
不管我倒下多少次
我都會再回來
我是暴力的印記
是生活的傷痕
我是塵世的公正之鏡
不屬于教堂
除了這種對于自我身份的直陳之外,更多巴西當代青年女性詩人選擇在對日常瑣事的描繪與反思中構建自己的形象與世界,每一個都獨具特色。當這種獨特的形象與世界結合起來,呈現的便是完整的當代女性詩歌圖景。或許是為了讓這個圖景更為具象、生動,《當今29位女詩人》中的每一首詩都配有作者朗誦的視頻。如此一來,公眾接觸到的就不僅僅是單薄的文字,而是由詩人的思想、聲音、形象、動作匯成的完整表達。
擂臺詩:邊緣青年之聲
擂臺詩(Poetry Slam)是一種新型的表演詩形式,起源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美國。參與詩賽的選手需要選擇自己的原創詩作,進行3分鐘的朗誦演繹,期間禁止使用道具或背景音樂,只能憑自己的聲音與肢體語言征服聽眾。2008年,巴西導演、詩人羅貝塔·埃斯特雷拉·達爾瓦(Roberta Estrela D’Alva)接觸到這一藝術形式之后,在圣保羅創立了巴西第一個擂臺詩團體“詞語自主領域”(Zona Aut?noma da Palavra,縮寫ZAP)。巴西擂臺詩的初次嘗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這一藝術形式在巴西的影響力迅速攀升。2012年,巴西迎來了第二個擂臺詩組織,即詩人艾默森·阿爾卡爾德(Emerson Alcalde)創辦的“吉列爾米娜擂臺詩”(O Slam da Guilhermina)。2017年巴西已有約50個擂臺詩團體,如今這一數字則上升至數百。

羅貝塔·埃斯特雷拉·達爾瓦
值得說明的是,巴西擂臺詩的發展與其國內推進針對邊緣群體文化教育的嘗試密不可分,每年的大型詩賽更被視為在階級、性別、種族等方面處于弱勢地位的群體向外發聲的絕佳機會,賽事主題也多與公民權利有關。自2018年起,吉列爾米納擂臺詩著手推進圣保羅公立中小學生的年度比賽,以鼓勵沒有條件上私立學校的貧困學子積極創造,以詩歌為媒介向公眾表達自我。經過篩選,前幾屆比賽中涌現的優秀作品以《圣保羅跨校擂臺詩賽:從街頭到校園》(Slam Interescolar–SP: Das Ruas Para As Escolas)為題,于2021年結集出版,該項目也獲得巴西文學最高獎項雅布提文學獎創新板塊的嘉獎。而在巴西全國賽事中,近幾年贏得最終大獎的也都是來自邊緣地區、具有黑人血統的女性詩人,如2017年巴西冠軍盧斯·里貝羅(Luz Ribeiro)與2018年冠軍貝爾·蒲安(Bell Pu?)。擂臺詩也成功幫助她們成為主流詩歌研究的對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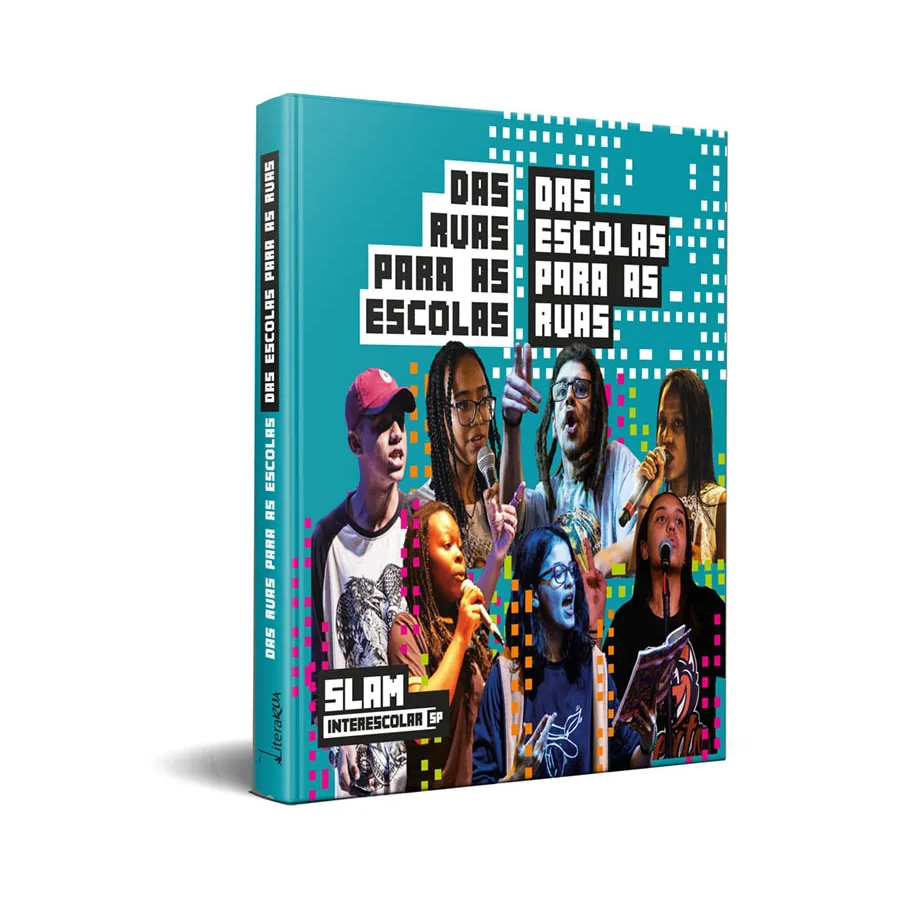
《圣保羅跨校擂臺詩賽:從街頭到校園》書影
事實上,僅在奧蘭達主編的《當今29位女詩人》中,就收錄了4名擂臺詩人,除里貝羅和蒲安之外,還有梅爾·杜阿爾特(Mel Duarte)和路易莎·羅芒(Luiza Rom?o)。這些詩人在巴西文壇積累了一定名望,其中羅芒更是憑借詩集《我們這里也留有石塊》(Também Guardamos Pedras Aqui,2021),不滿30歲便獲得雅布提文學獎最佳詩歌獎首獎,作品也當選為年度圖書。《我們這里也留有石塊》是一部富有實驗意義的作品,以對荷馬史詩的重述反思當代社會,通過使用留白、涂黑來增強作品的沖擊力,并帶有鮮明的口語特質。以上特點有助于充分調動讀者的情緒,而這些正是擂臺詩人的強項。以緊扣詩集標題的《安德洛瑪刻》(andr?maca)為例,可以一窺這些詩作的特質:
我未曾見過特洛伊
多多少少的廢墟
在大洋彼岸
我們這里也留有石塊
……
我被子彈射中臉部的伙伴是特洛伊
沼澤中的棄尸是特洛伊
追捕的領導者是特洛伊
女性謀殺的受害者是特洛伊
軍人法西斯主義者暴君
都在對特洛伊射擊
哲學法律西方
都源于特洛伊的滅亡
現在你理解我為何歸來了嗎?
在詩歌的后半段,作者表達了自己永不屈服的意志,以及與安德洛瑪刻跨越時空的團結。需要注意的是,這部詩集的每一首詩都以一個傳說中的希臘人物為標題,但所有標題卻都是小寫,體現出將經典形象融于日常的意圖,并達成了時空交錯重疊的效果。
羅芒的得獎無疑證明并提升了擂臺詩在巴西文壇的影響,從這種詩歌形式進入巴西,到創作者獲得國內文學最高獎項,僅僅經過了13年。考慮到擂臺詩的主要參與者為青少年群體,未來很可能有更多優秀的詩人詩作問世。而在肯定擂臺詩在國內影響力的同時,同樣不能忽視它對于巴西在國際舞臺發聲的重要意義。在法國舉辦的年度擂臺詩世界大賽中,巴西自2010年參賽以來總能取得前五名的優秀成績。盡管受限于語言等原因(參賽詩人以母語朗誦,評委大多數只能通過英語或法語翻譯了解詩作內容),所有的年度冠軍都來自于歐洲或北美,但來自巴西的邊緣女性詩人仍能獲得難得的國際曝光機會,說出通常情況下難以被世界“聽到”的話,正如蒲安在2018年世界大賽中所講的那樣:
很久很久以前,一個保守的巴西
白人是主人,黑人是財產
非洲人沒有靈魂
印第安人野蠻
根據歐洲人的觀點
這就是我們的文明巔峰?
他們甚至殖民了我們的思想
歐洲成為一切標準:
美麗、科學、進步
而巴西則五百年未曾成功
在此之后,蒲安同樣回溯了巴西女性在歷史上遭受的規訓與暴力,致敬了堅持抗爭的前輩榜樣,并將女性斗爭視為改變保守巴西的重要革命力量。這也正呼應了羅芒對于擂臺詩的看法:“(擂臺詩)不僅在形式上是革命性的,因為它重新強調了集體面向,在主題上也極具革命性,因為它在討論那些被長期禁言并從歷史中抹去的問題。”
結語:在“下沉”中上升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基礎教育的普及與電子媒介的興起,巴西的文學創作與閱讀機制發生了很大變化,體現出明顯的“去精英化”傾向。而詩歌由于篇幅相對簡短、適于朗誦演繹,“下沉”趨勢更加明顯,卻也賦予了弱勢群體更多以詩發聲的可能。無論是來自民間傳統的掛繩詩,還是長期被客體化的女性詩,又或是新興的擂臺詩,這些詩歌形式原本都只能處于主流創作的邊緣,如今則成為巴西詩歌不容忽視的組成部分,甚至是其中最具潛力與活力的部分。在這樣一個文學被不斷唱衰的時代,巴西當代詩歌卻以多元包容的方式觸及到更多民眾,并讓全世界聽到來自巴西的底層之聲——這種口頭性與集體性的勝利,無疑是當代巴西詩壇最重要的特征。


